新罗金冠与罗马玻璃
郝薇薇
距韩国最大港口釜山港约80公里的庆州,是一座只有25万人口的宁静小城。如果不是被选为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对很多人来说,庆州依旧是个陌生地名。
但回到1000多年前的朝鲜半岛新罗王朝时代,这方“喜庆之地”就已经是声名远播、人流如织的繁华都城和贸易中心了。在新罗统一半岛后的“黄金时代”(公元7世纪至9世纪),庆州人口一度超过10万,是古代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之一。
追溯历史,国祚绵延近千年的新罗王朝(公元前57年至公元935年)最繁盛的时光,恰是其与“中土大唐”往来频密的那段日子。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均田制以及长安城的星象规划、三重城形制等循着海路东渡,在半岛扎下了根。彼时的新罗,君王朝臣常以儒家经典为治国的指引,青年才俊也以赴大唐求学为人生的荣耀。
如今,汉风唐韵早已化为庆州的独特风貌——那是石窟庵寿光殿门柱上“少林门下事,不意生是非”的楹联;是佛国寺多宝塔浮雕上与西安大雁塔如出一辙的莲瓣纹;亦是韩屋村墙壁上结合《周易》和生辰八字预测年运的“土亭秘诀”。看过这些风景再来庆州博物馆参观,也就不觉得有多新奇了。
不过,仍有出乎意料的收获。庆州博物馆展览序言部分开宗明义介绍“新罗”的来历,竟是取自汉语“德业日新,网罗四方”。不过,博物馆方面进行了颇具现代性的阐释:“德业日新”意为“改革与创新”,“网罗四方”相当于今天的“全球化”。想想倒也贴切。人们通常将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其实,比这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新罗,与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往来紧密,何尝不是早期全球化的形态呢?
不久前,韩国政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赠送了一座新罗金冠模型作为国礼,其真品就珍藏在庆州博物馆。据推测,金冠主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定国号为“新罗”的智政王。镶嵌在金冠上的数十颗曲玉则大有来历。这种形似月牙的饰品,又称“勾玉”,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是权力和声望的象征。传统观点认为,勾玉借贸易和移民由日本列岛传播至朝鲜半岛;也有学者提出,勾玉的源头其实在中国,它们与中国东北地区兴隆洼、红山文化中常见的玉、C型动物玉器有着重要联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勾玉原本是长江下游古越人的文化符号,随玉石交易传入日本列岛濒临日本海的一侧。如果以上说法中无论哪一个被证实,那么“东亚的全球化”都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
庆州博物馆另一类重量级藏品当属罗马玻璃。这是另一个生动的全球化故事。罗马玻璃主要是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各地工坊生产的钠钙玻璃制品。这些晶莹剔透的杯碗经地中海、黑海、中亚草原、中国腹地进入朝鲜半岛,在新罗人心目中是比黄金还珍贵的稀罕之物。
庆州博物馆的展陈中,有一只出土于新罗王陵天马冢的蓝色玻璃杯,很可能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制造”,其器形与位于中国南京的象山7号墓出土的玻璃杯相似。玻璃是古代世界最受欢迎的全球化产品之一,千百年来,正是那些玲珑的玻璃、华美的丝绸、温润的瓷器、馥郁的香料,如磁铁一般将英国诗人吉卜林笔下“尾碰不到头,二合不成一”的东方和西方吸引在了一起。
无论是新罗金冠还是罗马玻璃,这些“古早”的全球化故事,正是人类从分散走向聚合的大潮流的见证。只是,当特朗普收下新罗金冠的复制品时,他是否知晓它背后这般多彩的历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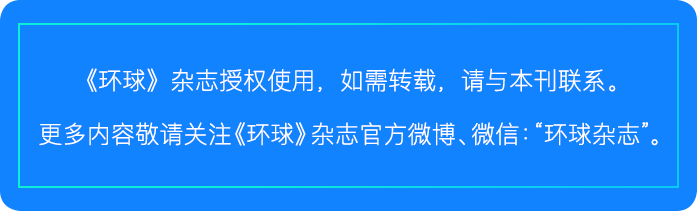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
